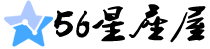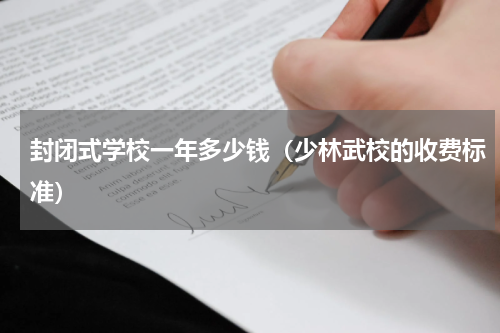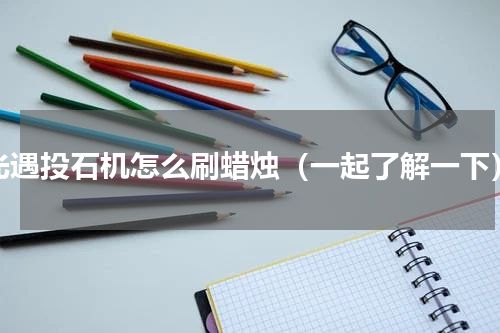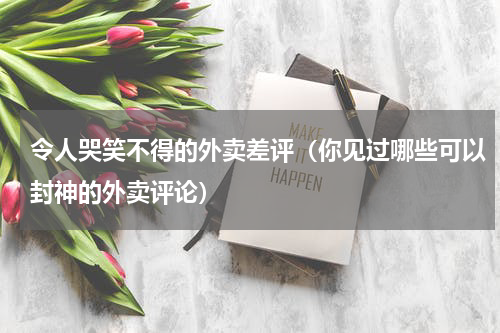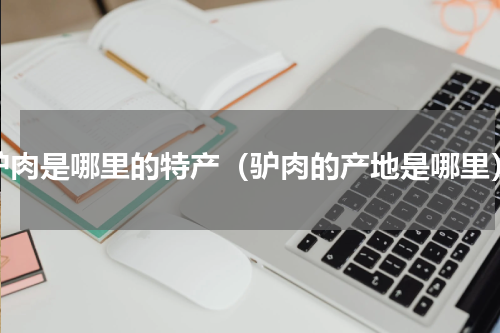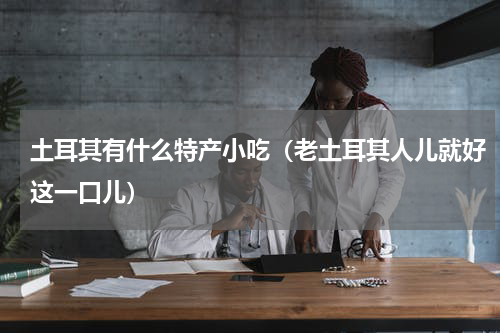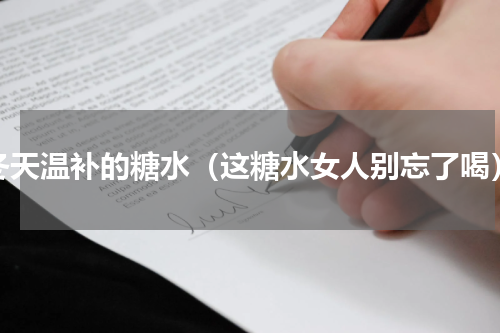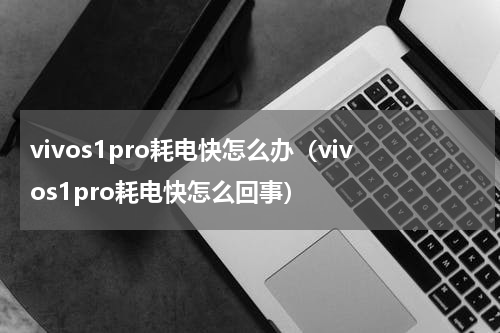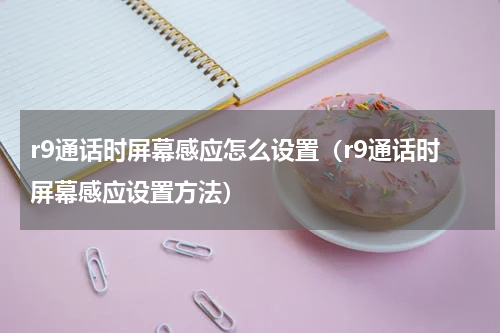几经周折,把罗养儒的《云南掌故》买来瞧瞧,拿到之后,爱不释手。《云南掌故》一经出版,立刻洛阳纸贵,起初售价四十八元一本的《云南掌故》,被收藏市场炒到了好几百元。笔者认为,除了史料意义外,取决于《纪我所知集》的通俗、有趣和文字的深刻。从1879年到1911年,罗养儒由一个婴儿步入而立之年。墨西哥人认为,人的终极死亡是最后一个记住他的人,把他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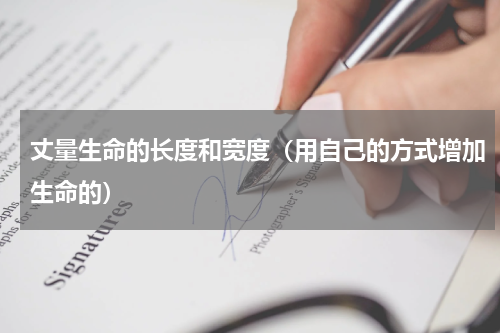
大学时代,读作家于坚的散文说,“罗养儒是第一个将晚清时期云南市井生活,描写得像天堂一般的作家”,我好奇“天堂”究竟是怎样一个美法?几经周折,把罗养儒的《云南掌故》买来瞧瞧,拿到之后,爱不释手。每晚宿舍关灯,我打着手电筒观看,与东晋大儒车胤的囊萤夜读蛮像。上个月,我做客五华讲坛讲《罗养儒笔下的云南近代社会》,特意找来大学时买到的那本《云南掌故》,尽然被我翻看“散了架”。
罗养儒,又名继春,字兆熙,号古粤龙平畸士,广西省昭平县人,生于1879年。罗养儒年少时,曾随在云贵总督府做幕宾的父亲罗守诚举家迁往昆明,后随家人游宦,游历云南二十多个州县,记录下了大量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事和民俗习惯。晚清时期,罗养儒曾中过秀才,后回广西昭平老家参加乡试不第,此后再无心科举。青年时代他回到云南,先后就读法文学堂、云南法政学堂讲习所,他考取过中医师执照,做过领事馆翻译、学校教员、报馆主笔,还自办过报纸、办过安全火柴厂和电机碾米厂等近代新型工厂。晚年以义务为人看病、笔耕著述为乐。1956年,受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常言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从罗养儒先生丰富多彩的一生不难看出,养儒先生不仅读过万卷书,行了万里路,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特别是他办报、做主笔的经历,让他有机会与社会不同层级的人接触,这也为他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使这部“亦耗尽十年气力”,记录罗养儒“亲闻、亲见与亲历”的《纪我所知集》,更加鲜活、更加悲悯与真实。
从199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组织专家对罗养儒的遗稿《纪我所知集》展开点校,“当时因为各种原因删掉了部分章节”,学者李春龙“另拟书名《云南掌故》付梓”,使罗养儒先生的名字重新回到公众视线。《云南掌故》一经出版,立刻洛阳纸贵,起初售价四十八元一本的《云南掌故》,被收藏市场炒到了好几百元。尽管出版社曾多次再版,但这部书一到书店,又立马被抢售一空、屡屡供不应求。2018年2月,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云南文丛,重新点稿书稿,并恢复书稿的原名《纪我所知集》,收录的文章也从删节版的421篇,增加到了485篇的全本。
一部纯文字的掌故为何如此卖座?笔者认为,除了史料意义外,取决于《纪我所知集》的通俗、有趣和文字的深刻。它似一幅云南版的清明上河图,是一部美轮美奂的云南十二时辰,更是一曲浮华盛世的挽歌。
从1879年到1911年,罗养儒由一个婴儿步入而立之年。在这段时间,云南境内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得以平息,岑毓英等循吏,通过近代工业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引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元气”有所恢复。用罗养儒的话说,当时的“昆明街头即行于街头的人,亦无一愁眉苦眼者,有则遭遇大不幸的事情”,市民生活“是之谓衣食有着,生活安定”。
观察一个城市的温度,往往要看这座城市,民众发自内心地“真善美”,《纪我所知集》里记载,晚清时期昆明城里大户人家会在家门口摆上一口大缸和一个缺口的碗,在大缸里盛满清水,供路人免费饮用。大户人家为什么要选择缺口的破碗供路人取水呢?天热口渴,大口饮用凉水,容易伤身体,“碗有缺口,当然以大拇指按入缺口,大拇指上有一少商穴”,既可以按摩穴位、减缓喝水的速度,保护喝水人的身体;“以缺碗置于板上,防人窃取此碗而去”,更能保证施水活动的长期进行。做好事不仅为受助者着想,同时保证了善行义举的持续性,见微知著,由此可见,近代云南人骨子里的善良、厚道,也从侧面解释罗养儒对这一时期生活的特别眷恋。
近代云南社会,列强入侵、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明激烈碰撞,浮华盛世背后,社会危机四伏。《纪我所知集》里记录了很多反映清末社会危机的文章,如一个长相怪异的“大头宝宝”,因为奇怪的长相和口技声,而被愚昧、强权扼杀;腾越厅同知谢谨,不思进取,整日吸食鸦片,耗费巨资打造出三十六支以“知府”“道台”“巡抚”“总督”等官职命名的精美烟枪,大口吞云吐雾,满足其官瘾和烟瘾;石屏举人朱筱园,贵为云南巡抚的座上宾,仅因为在酒楼批评地方恶势力“实大有危害于社会处,似不可不清除”,便被人“概以老拳相敬,而又一言不发,只是频频殴击”。朱举人写信请昆明县及文武总查缉凶,终无所获……罗养儒先生用诙谐、生动的文字,记录了清末云南地方恶势力的猖獗,官场腐败及社会管理的失控,民众无法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党腐败日剧,“金圆券改革”失败,战争、苛政、飞涨的物价,令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罗养儒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过着“有工得一饱,失业饿断肠”的凄苦生活。
罗养儒先生于1956年春完成《纪我所知集》书稿,至今已有65年,重读这部经典著作,需要我们理性地思考历史。正如在2014年2月24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既不要片面地讲厚古薄今,又不要片面地讲厚今薄古”。对待历史,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不可复制,理所当然的将过去想象得美好无比,也不能把过去的历史片面地解释为一无是处的“糟粕”。
人生短暂,相比星辰大海,人的生命,尤如白马过隙。我从哪来?我到哪去?一直是让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元问题。墨西哥人认为,人的终极死亡是最后一个记住他的人,把他忘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繁衍后代,或用自己的文章、故事、生活,让更多的人记住自己,以增加生命的“长度”。未来怎样?我不知道!我只想说,人只活一辈子,我崇敬像罗养儒先生这样的人,记我所知,真实记录下生命中点滴有趣或难忘的片段,用自己的方式增加我们生命的“长度”。